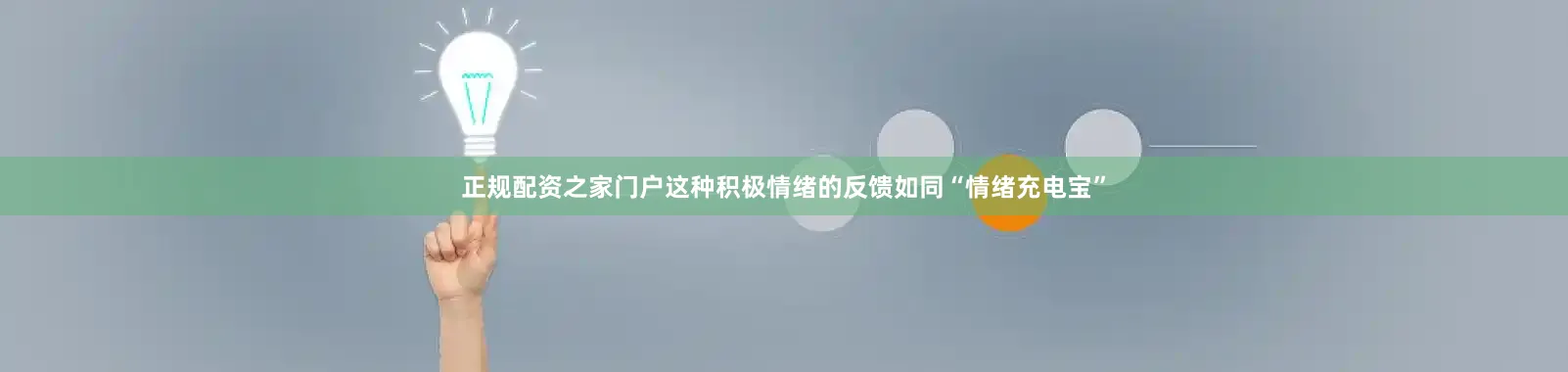陈可乐觉得自己有时就像一只鬼,在油麻地到处飘荡。
夜晚,它穿着银色反光连体衣,戴着手套,脸上涂满蓝银色的颜料,眉毛是两道黑色的、柔软的线条。它有一双悲伤的眼睛,比起鬼,更像是误入地球,迷了路的外星人。
打扮成这样,是为了表达内心的黑暗和一种异乡人的感受,陈可乐说。作为一名非二元性别者,无论是“它”的代名词还是平日装扮,都是在发出一种邀请:邀请我们更好地了解陈可乐和它长久居住的社区——油麻地。

陈可乐在油麻地
2016年至今,艺术家陈可乐和朋友陈玉峰发起了围绕街区命案展开的导览团《在油麻地的两万种死法》,带领人们游走在城市的缝隙,重新思考死亡背后的社会面,以及一个社区如何与创伤共处。
建筑、历史、悬疑、想象…...香港是一个由神秘空间交错形成的复杂地区,这里从来不乏都市传说与类型命案,人们在具体的空间中构筑起自己对于香港的认知,而那些未曾涉足的空间,则给予了足够的想象留白。
在NOWNESS Paper夏季刊“香港折叠”专题中,我们试图走近这些空间、破除迷雾。这个过程就像拿起一把解剖刀,切开香港不同时期的历史和社会面后,悬疑的终点指向人们内心深层的共情和恐惧——殖民的统治,逼仄的生活,无根的飘零者。
在生与死、规训与越轨、记忆与遗忘的缝隙间,香港浮现出另一面。这是第一篇,油麻地。

切开悬疑的迷雾
2025年5月末,一个闷热的夜晚,陈可乐带着NOWNESS走访了这条路线。
在两个小时的行走与讲述之中,街灯昏黄,拖车“哐当哐当”不停,街市传来阵阵骨肉与果蔬的气息,维多利亚港逐渐褪去繁华,情杀、意外、抛尸、自决……城市的残酷一一显现,死亡是一纸极端的宣言。
人死后,可否会往生?如果怨念不散,是否会变成鬼,在现世徘徊?如果世上真的有鬼,那他们大概率住在油麻地,那里本就藏污纳垢,在后巷、砖缝、垃圾堆和那些密密麻麻的唐楼之间,有很多可以安生的地方。

油麻地是香港最古老的街区之一。据记载,这里早年聚集着为渔船出售桐油、修补麻绳的商铺,因此得名“油麻地”。
它几乎一直是贫民窟的代名词。这里鱼龙混杂,流浪汉睡在公园的帐篷里,内地留学生合租房楼下可能就住着黑社会,奶茶店旁那扇不起眼的铁门后,也许就是挂着粉色灯牌的妓院。
在房价骇人的香港,这里也提供着可负担的租价。“这就是一体两面的事情。”陈可乐喜欢这个混乱复杂,也包容着边缘群体的地方,“如果想要清洁与干净,就不会住在油麻地”。


《黑社会》,2005
陈可乐在油麻地生活多年,熟知着这里的街巷楼宇,也了解这里的肮脏、混乱和贫穷,但依旧停留于此,倾听“鬼魂”的哭嚎——那是有别于新闻与官方文件,来自街区与居民的叙事。
最早是在2010年,大学期间的陈可乐为了节省租金,搬进油麻地的一个洗衣店阁楼夹层。那里狭窄逼仄,如同哈利·波特在他姨妈家居住的空间,“而且还是违建的”。
这样的事在油麻地算不上什么。这里街巷四方纵横交错,楼宇密集——高度密集的社区生活把居民紧密地连接在一起,也让死亡如影随形。一些命案就发生在人们每天经过的便利店或垃圾站,曾有坠楼者的手臂飞脱而出,落在街边老人下围棋的棋桌附近。


《香港制造》,1997
面对死亡,油麻地有麻木与无情的一面:陈可乐指着一扇三楼的窗户说,曾经有位厌世的老人将自己吊死在那里,过了一整晚都没有人发现。这些死亡既无法被清除,也无须被粉饰,它是街区记忆的一部分。
但有时,人们会用自己的方式作出回应。在陈可乐曾经居住的楼后面,有一名男性残忍地杀害了一名年仅15岁的女孩,并将她赤裸地塞进垃圾袋里弃置。发现尸体的清洁工自掏腰包,为逝者购买了衣服与鞋子,在垃圾站里为她做了祭拜。
垃圾站臭气熏天,人们往往会捏着鼻子绕行,但那里也存在着一个人给予另一个人的尊严。这里的景象原始、粗粝,充满都市文明中难以启齿的部分,但也都是不可回避的城市的真实。在油麻地,陈可乐与这些命案、亡魂为伴,通过讲述,也在寻找自己与这个所生所长,却日益陌生的城市的联系。

油麻地生活着大约有两万居民,“两万种死法”的导览名称借用了这个数字,以几乎开玩笑的方式,提醒着我们生与死的模糊边界。
这个项目起始于陈玉峰对自己的发问。她也居住在油麻地,不但不害怕命案,反而更想知道:“为什么他们会死在这里,而我没有?”为了解答这个问题,他们翻阅资料、梳理命案的发生经过,试图从中辨识出背后的社会机制。
陈可乐承认,作为导览团,形式上难免有着对命案的“凝视与猎奇”,但比起观看,自己更想传达的是那些命案背后的荒谬。它们如同镜子一样,反射出许多社会边缘群体的脆弱,死亡正是社会和制度不公的回声。


《香港制造》,1997
2016年,在油麻地地铁站附近的一家711便利店里,店长因制止一名男性顾客偷窃,被一刀捅至丧命。事件发生正值傍晚六点,是下班放学的高峰期,案件一经报道立即引起了公众的恐慌。
很快,有流言称凶手是南亚难民,这个未经查证的说法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,并演变成了一次针对难民的排外活动。直至真相发布,凶手其实是来自加拿大的越南裔游客,但即便如此,事件的一周后,这里仍有反难民的示威。
“他们想把整个罪责推到难民身上。”陈可乐说,“但其实这一片根本没什么难民。”恐惧制造仇恨,仇恨让暴力转向脆弱的社会群体。而导览团想做的是呈现命案的原貌,讲述街坊的真实记忆,让人们看清暴力的起因和走向。

在香港,Hello Kitty 也成为一种悬疑符号
还有一些案件源于根本“没有选择”的人生。其中最常在导览中被提起的,是一起外籍女佣弃婴案。
2014年,因为害怕被解雇,一位27岁的外籍女佣将分娩时夭折的婴儿遗弃在油麻地地铁站。事件发生的两年后,另外一名外籍女佣控告因怀孕而解雇她的雇主并胜诉。
在香港,大多数家庭会雇佣来自东南亚等国家的女性做家务工作,她们被绑定在雇主家中,因此时常遭遇不公的对待——直到2022年,在相关机构的调查中,香港84%的雇主仍认为可以因为外籍女佣怀孕解除雇佣关系。
对于那个最开始的问题——为什么身处同一空间,死的是他们,而不是我们?陈可乐很坦诚地承认自己拥有特权,“大部分的暴力是制度性的,并不会落在我们身上。”便利店外大喊“难民滚出香港”的示威人群在行使暴力,以怀孕为由解雇外佣的雇主也在实施暴力,“暴力是有施加对象的”,这是导览团希望能真正传达的一点。

从2016年起,陈可乐大概已经带过100多次导览团——与社区交流,与社群共存,是导览团留下的重要遗产,也是至今都无法割舍的生活方式。
陈可乐出生在远离市区的新界元朗,随后决定在油麻地安家,也确实在这里建立了一种生活,一路导览下来,不时会碰到朋友,挥手招呼。
但这些年来,它觉察到周边社区的氛围“越来越差”,油麻地一直以来混乱却包容的生态正逐渐被侵蚀。在我们就餐的茶餐厅附近,原本设在垃圾站上层的露宿者之家,多次被政府驱赶。而另一家餐厅因为把桌子摆在街上而屡屡遭到投诉,甚至一度被威胁吊销牌照。

陈可乐在平安大楼
陈可乐对油麻地的每一尺、每一寸的故事和历史都如数家珍,同样也由此见证了政府是如何以“清洁、整齐和安全”的借口不断推倒老旧的房屋,剥夺社区的空间。
但在那些管制的缝隙中,仍有一些喘息空间。社区的年轻人保住了那家被投诉的餐厅,他们挨家挨户发问卷,收集意见,这些在法庭上变成了真实的支持。
这样的相互包容与帮助正是一种微小的抵抗,允许附近的混乱和野蛮,也就是允许贫穷和脆弱可以在这里生存。陈可乐欣赏这样的街道生活,因为“街道应该是一个可以停留的地方,而不仅仅是一个通勤通道”。

平安大楼的信箱
陈可乐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回馈这个社区:早期的天台导览介绍20世纪70年代逃港难民的故事,油麻地的导览揭开社区的伤痛,未来准备创作的一个关于外卖员的项目,都是属于自己的微小抵抗。
生存、抵抗和死亡,在这个街区不断上演,官方的记录里很少有他们的影子。被抛尸的女孩、被遗弃的婴儿、被驱赶的露宿者,是朱迪斯·巴特勒所说的“不可哀悼的生命”,而陈可乐的导览就是试图让他们再次被看见、被听见。
这些“鬼”整日游荡在油麻地的街巷之中,街道肮脏混乱,却又包容了它们,这里有最新鲜的水果和蔬菜,老板会笑着,大声跟你打趣,现炒的鱼香茄子有着诱人的香味。


《三命》,2025
采访拍摄结束,已经是深夜,我们与陈可乐简短地挥手作别。一路上的疲惫让它下眼睑的黑色水彩往下晕开,恍惚会让人以为是在流泪。我目送着它银色的身影,逐渐融入黑色的、熙熙攘攘的人群。在路口处,陈可乐遇见了一位朋友,他们随后一同肩并着肩,消失在了道路的尽头。
这些人与人之间,微弱却偶尔又格外坚定的联系,或许就是油麻地的灵魂。他们互相陪伴,也守护着自己的土地。




NOWNESS Paper 2025夏季刊邀你一起揭秘悬疑档案:为什么要伪造一个已经消失的国度?如何跟油麻地的鬼魂一起散步?如果和AI动了真情,要怎么离开这场戏?明知魔术是一种欺骗,观众为什么还要沉溺其中?听,你会如何形容一声枪响?是什么让章子怡嚎啕大哭、浑身颤抖?创造死亡搁浅的小岛秀夫,也会害怕死亡吗?



配资平台开户,启天配资,郑州配资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